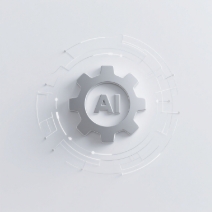“不用纠结,现在是否到了具身的 GPT-3 时刻。”
20 年前,新加坡人陈维广来到中国时,通讯录里几乎没有联系人,普通话也不流利。
陈维广那时已在美国科技圈工作十余年,在 IBM 经历了从大型机到 PC(个人电脑)的转型,后于 2000 年加入 Bluerun Ventures,完整亲历了千禧年的互联网泡沫。当越来越多硅谷华人科学家和工程师回到中国,陈维广投身尚未兴起的中国风险投资市场,后于 2008 年成立蓝驰创投。
此后 20 年里,蓝驰没有成为名声显赫的投资机构:京东、字节、拼多多、快手、小米、小红书、B 站……互联网浪潮里的明星,蓝驰一个都没投。但蓝驰又一直留在 VC 市场,管理规模从最初的几千万美元扩张到 200 亿元人民币,并在 2008 年、2022 年的市场低谷中逆势大额募资。
直到新能源浪潮到来,蓝驰才获得了一个不需要解释的知名项目:理想。支撑这家基金 “慢慢长大” 的,更多是一些知名度不是最大、但带来了不错回报的公司,如赶集、高仙、云圣智能等。
陈维广说:“基金的生命力,最终要兑现为 DPI(投入资本收益率)。” 一位投资市场人士称,蓝驰有严格的出手价格和退出纪律。
在新一轮生成式 AI 和大模型热潮中,蓝驰一改低调,开始频繁出现在头部 AI 项目中,且常常是首轮或早期投资者——自 2021 年起,蓝驰陆续投资了大模型公司西湖心辰、月之暗面,AI 应用公司 Genspark、沐言智语和与爱为舞等。
在具身领域,蓝驰出手尤其凶猛,投资了智元机器人、银河通用、灵初智能。其中,蓝驰连投智元两轮,银河和灵初,都是在天使轮投资。
今年春天,蓝驰又与启明联合领投了它石智航,这家具身智能公司的首轮融资额破纪录地达到 1.2 亿美元。

从上至下,为蓝驰投资的银河通用、智元机器人和灵初智能的产品。
蓝驰押注的是:人口老龄化背景下,中国制造业对具身智能有长期刚需;中美竞争之下,中国产业必须在 AI 与实体经济融合上构建护城河。
而眼前的现实是:具身智能技术仍在早期、产品不成熟、大家都还在试场景。朱啸虎的话引起了更多共鸣:“现在人形机器人就会翻跟头”、“他们说的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客户”。
陈维广则相信,入局具身智能,现在并不早。在理想上,他看到了技术落地前慢后快的演进曲线:“如果晚了,就只能跟大厂拼资源了,我们选择支持早上牌桌的创业者。”
围绕具身智能的机会和蓝驰过去的科技投资思考,我们访谈了蓝驰创始合伙人陈维广和管理合伙人朱天宇。
理想是目前蓝驰最知名的项目。投资理想的朱天宇,于 2009 年加入蓝驰,2015 年升为管理合伙人。
陈维广是 60 后,与他同期入行的不少投资人已在近年离开一线。陈维广仍自己看项目、见创始人。他说,蓝驰不是兔子,是乌龟:“慢慢迭代,但不断往前爬,一步步走到今天。”
从 Feature Robot 到 Smart Robot
晚点:蓝驰创投成立 20 年,不过不少人说不出对蓝驰的明确印象。你自己会怎么表达蓝驰是谁?
陈维广:我们是一家慢慢成长,持续迭代认知的创业公司。
晚点:蓝驰最成功的投资是哪些?
陈维广:这要看怎样定义成功。每个阶段我们都有代表性项目,如果是品牌知名度,理想汽车显然算一个。我们当然追求头部项目和高回报,但成功不该只看名气,基金的成功应该是一种整体的成功。
晚点:理想汽车现在要成为 AI 公司,创始人李想现在也重点抓 AI。作为理想投资人,你们怎么看这个转变?
朱天宇:当然是更看好了。他选了一个更大的战场,而车只是入场券。其实 2022 年时,理想就已经明确了市占率、造血能力、供应链能力等阶段性目标,这都是为 AI 打基础。理想内部早就开始定期讨论 AI 带来的正负面影响,这是持续思考的结果,不是突发奇想。
陈维广:我们最近正好在做复盘,看到了当年投理想的立项材料。当时天宇在推这个项目时,就不是以电动车视角,而是自动驾驶的视角。当时我们判断自动驾驶一定会发生,但关键是有没有数据。第三方难以拿到主机厂的数据,而理想这样自己造车、自己布局智驾的公司则可以形成数据闭环,这是我们的信心来源。2017 年时,理想就已在布局自驾了。
晚点:蓝驰近 3 年频繁出手 AI ,既投了大模型公司西湖心辰、月之暗面等,也有 AI 应用公司 Genspark、沐言智语、与爱为舞等;尤其在具身领域,你们是国内出手最集中的机构之一,投了智元机器人、银河通用、灵初智能、它石智航。而 2016 年的那波 AI 热潮中,CV(计算机视觉)四小龙你们一家都没投,为什么变化这么大?
朱天宇:核心是 “场景”。上一波 CV 擅长做评判式 AI,但落地场景有限。这一波我们更关注 NLP(自然语言处理),从 GPT-1 开始就在跟踪它的进展。2020 年 GPT-3 出现时我们就在讨论它的突破意义。那时候我们已通过一些项目发现它在私域数据训练上效果显著。我们 2021 年就投了西湖心辰,创始人蓝教授就是轻量级模型 ALBERT(Google 2019 年推出的一个 Transformer 架构的语言模型) 的作者,我们很早就看好他的研究方向。
晚点:从 NLP 到大模型,再到大力投资具身智能,这个过程是怎样的?
朱天宇:ChatGPT 出现后,我们意识到基础模型的突破是语言作为知识枢纽的能力跃迁,这比过去的 PC 和移动互联网更颠覆。因此我们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层全面布局。
2022 年底,我就提过 AI+3D 交互 +Robotics 的 “三浪叠加” 将孕育未来 30 年周期中的 Big Thing——所以蓝驰不是割裂地在看 AI、机器人等,许多赛道看似独立,其实都是基于同一个底层逻辑。
所以这之前我们就在投 Robotics,只不过是 feature robot(服务相对特定场景),现在是 smart robot。今天的具身智能,就是融合 AGI、空间计算与 Robotics 的成果。
晚点:同一个底层逻辑指什么?比如现在大量涌现的 AI Agent,它和具身智能、空间智能有共同逻辑吗?
朱天宇:Agent 和具身智能不是割裂开的。从 Agentic System(代理型系统)的整体视角看,它正沿着 instruction(指令) 和 action(动作)的方向演进。
当 Agentic System 驱动数字化能力时,会催生如 Genspark 这样的 Agent 产品,这是搬运比特的数字工具,也就是 computer use;而当其驱动物理能力时,就会产生具身智能,这是搬运原子的物理工具,也就是 tool use。
这就是为什么当行业在热议人形时,我们最关注的是具身脑、而不是形态,因为无论是数字工具还是物理工具,都需要用大脑来调用。
陈维广:这个思路也能解释蓝驰对于 AI 的信心和笃定。移动互联网的价值在于连接,而 Agent 能更进一步交付结果,会创造出 10 倍于移动互联网的价值;具身智能又要进一步完成真实世界的任务,创造的价值又会是 Agent 的 10 倍,这是百倍于移动互联网的市场。
“中国发展具身智能有比较优势,不用纠结现在是否到了 “GPT-3.0” 时刻”
晚点:相比大语言模型,具身在技术上更早期,为什么蓝驰认为现在就是一个投资时机?
陈维广:车是 “轮子上的机器人”,具身的技术路径可以参考车的发展。2017、2018 年,自动驾驶系统还依赖高精地图和大量标注,无法解决 corner case 。但今天,端到端普及,智驾系统体验大幅提升。在具身智能领域,很多团队也在探索在 VLA(Visual Language Action model 视觉、语言、动作模型)端到端思路,让系统更通用,这是个值得投入的方向。
晚点:也有观点认为 VLA 做不出具身基础模型。比如今年 GTC 大会上,Meta 首席科学家杨立坤(Yann LeCun) 说现在的大模型路线很难解决物理世界的 AI:“token 不能表示物理世界”。你们看到了 VLA 哪些被验证的迹象?
朱天宇:确实还在探索期,但已有迹象:智驾已从感知端到端,拓展至 P&N(规划和控制),最终实现系统闭环。机器人比车复杂,需要更多模型、算法与工具链,但我们相信它会像自动驾驶一样逐步收敛。现在是 “准备期”,不是 “结果期”,但市场体量巨大,我们要先占位。我们之前亲历过理想训练体系的迭代,看到系统能力在闭环体系中持续爬坡——这给了我们对具身的信心。
晚点:2016、2017 年时,自动驾驶在训练过的公开道路上,可以自行行驶数十分钟。而机器人现在要独立动起来几十分钟、完成一个现实生产或生活里的复杂任务还非常难。
朱天宇:能不能 “动起来”,要从不同维度来看。机器人能力分为三层:locomotion,也就是运动控制;manipulation,就是操作能力;还有灵巧操作能力,这需要灵巧手。
locomotion 相对积累得久一些,宇树等公司已经做得比较好。但现在行业更关注后两个能力,它们对完成复杂任务更有价值。这两个能力目前还在发展中。
陈维广:还有 “第四层” 能力,大脑,这包括识别、学习和泛化能力。其实很多场景里,也不需要有双足运动能力的机器人,轮式底盘和高效抓取的组合就够了。我们更看重能力组合与任务的适配,而非单项指标。
朱天宇: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持续 bet 赛道上的多个优秀团队,因为不同团队有不同解题思路,最后能找到的场景也不完全一样。
晚点:因为你们投的具身公司够多,正好能观察到不同的解题思路,比如在获取数据上,银河通用侧重仿真,智元则在用 1000 台机器人采集真机数据。你们会从哪些维度判断这些不同选择的进展和潜力?
陈维广:其实这些创始人都不会固守一种技术组合,而是会根据技术发展和场景需求动态调整。比如银河也有真机数据,只是比例侧重不同。关键在于最终能否处理真实场景、成本是否合理。
晚点:不少早期科技投资机构更倾向一个领域或方向里只投一个公司,蓝驰在具身智能领域却投了一批公司。这是为什么?
陈维广:因为这个机会太大了,与其说逐一去分辨不同团队的技术组合,我们更大的判断是要重投入具身赛道。
这背后的底层判断是:中国发展具身智能在全球有比较优势,尤其在供应链、工程效率上远优于美欧,现在大家去走访 PI(美国具身智能公司 Physical Intelligence)或 Figure,老美都会说,“具身肯定你们还要比我们迭代更快”。就像当年我们押中智能驾驶一样,我们相信这里能跑出下一代的全球性公司。
朱天宇:具身既包含现在 AI 的进展,又结合了中国的比较优势。投具身智能,是在当下中国市场顺势而为的选项。
晚点:具身智能投资的最大风险是什么?
陈维广:技术路径复杂、场景适配难度高,但这些都逐步能被解决。
朱天宇:有公司倒在 PMF(产品市场匹配) 出现的前夜。
晚点:也有投资人总结,现在具身的挑战不是 PMF,因为它还在 TPF 即技术到产品工程化的匹配阶段。最大风险是,3、5 年后,大家还是找不到做出足够通用的具身基础模型的方法,这就谈不上后面的更通用的机器人产品和商业落地。
陈维广:现在具身智能的挑战肯定有很多,但我们更关注长期趋势。一是中国制造业对具身智能的长期刚需;二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,智能机器人是结构性解法;三是中美竞争格局下,中国必须在 AI 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上构建护城河。
大模型加持下,智能机器人一定会有新的规模化落地机会。所以不用纠结现在具身智能是不是到了 GPT-3.0 或 3.5 时刻,这没那么重要。如果入局晚了,就只能跟大厂拼资源了,我们选择支持早上牌桌的创业者。
晚点:重押具身智能这类与制造业结合的 AI 赛道,是否也和蓝驰募资的币种的变化有关?
陈维广:我们是双币基金。这和币种没有关系,我觉得 VC 还是要冒风险,要尽量投早。
“找到一边赚钱,一边赚数据的具身智能场景”
晚点:前段时间朱啸虎说:“这几个月金沙江在退出一些过去几年投的早期具身智能项目”,原因之一是现阶段看不到商业化的客户。你们有看到哪些具身智能的潜在商业场景吗?
朱天宇:很多人期待具身机器人先落地在家居场景,但我们更看好工业等没那么性感、科幻的领域。比如我们投的它石、智元,已在探索具体场景,两三年内可能会出现能实际交付的 “机器人岗位”。
ChatGPT 也不是 GPT 的第一个 PMF,它是第一个爆款 PMF。在 GPT-3.5 之前,已经有一些公司、应用是基于 GPT-3 在做了。现在模型创新的速度还在加快,具身智能可能更早实现 PMF。
晚点:那具身的第一批 PMF 可能会是什么?
朱天宇:可能是一些非标的,不那么在意产线节拍的工业场景,或是一些很有痛点的消费场景。
晚点:比如呢?
朱天宇:等做出来再说,能做出来才有说服力。还是要给创业者更多保护和探索空间。
晚点:那么完整总结一下,适合智能机器人的场景可能有什么特点?
朱天宇:关键是能在完成任务的同时,反哺智能成长,最好是能找到一边赚钱、一边积累数据和智能的场景。
晚点:以你们投的银河和智元为例,它们都推出了轮式双臂类人形机器人,目标场景之一是工业生产,而工厂里已经有很多 2016 年之后逐渐进入产线的智能化机器人和设备,它们也有 AI 感知、力控等能力,能适应环境完成一些相对灵活的任务。那么新一批具身智能公司的产品在这些场景的独特竞争力是什么?
陈维广:如果去到工厂,你就会惊讶,现在很多工位还是不能用所谓 “智能化协作机械臂” 来替代人,许多非标任务还是得靠人。这是更通用、灵活的智能机器人的机会。
朱天宇:其实这两类公司都有机会。关键在于团队是否有转型能力和场景构建能力。即使是从 feature robot 起步的公司,如果有合适团队,能找到真实场景,也可能从规则驱动跨越到模型驱动;反之,讲很大智能故事的团队,如果缺乏 know-how 和执行力,也难以真正落地。
晚点:具身发展很快,你们经历过打破已有认知,重新判断的过程吗?
陈维广:肯定有,比如过去我们更看好真机数据,但最近看到仿真数据质量在提升,在重新评估它的价值。
晚点:既然之前有这个认知,为什么在天使轮投资了银河通用?
陈维广:我们首轮投银河时,判断它也需结合真机数据。后来团队迭代很快,用仿真方法也做出了成果。
朱天宇:其实我们之前也不是不看好仿真,而是认为不应执着于某种解法。这正是风险投资的本质——在不确定中寻找方向。我们复盘时也常问自己:是否在一些判断上收敛太快?是否被既有经验限制了思维?
晚点:投了多类 AI 公司后,你们会怎么总结大模型和具身智能投资的不同?
朱天宇:大模型范式还是由美国先定义的,具身则是中国团队自己在摸索着往前跑,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一点。
晚点:特斯拉的 Optimus 没能定义具身的范式吗?
朱天宇:它有启发,但不代表全部路径。现在美国投资人也普遍认为,中国会在具身上跑得更快。
晚点:聚焦和多方向探索,怎样才能跑得更快?
朱天宇:资源有限下建议聚焦。但正因为现在还没有共识性的范式,优秀团队要有持续做技术判断的能力。智能机器人又是一个软硬结合,涉及算法、工程、数据等能力,需要计算机、机械工程、材料、能源等多产业支持的跨界行业,我们也很在意团队能力的完整性和综合性。具身创业公司不能只擅长单点技术,也不要迷信某个技术方向。
晚点:你们投资的智元,作为早期公司最近正式发布了面向不同场景的 3 个产品线,分别由 3 个不同的总裁负责。这足够聚焦吗?
朱天宇:每个公司的禀赋不同,智元选择多线并行试错,是因为它有丰富的资本和人才储备,能支持这种高强度迭代。这能帮它尽快找到一边赚钱、一边赚数据的场景。不是所有公司都有资源这么干。
陈维广:这三条线其实针对不同的客户群,有的偏头部客户定制,有的侧重长尾探索,智元也正在摸索不同需求、 不同场景的过程中。
晚点:具身智能的下一个赛点会是什么?谁先做到什么事会和其他公司拉开差距?
朱天宇:就是找到有客户买单、且愿意持续买单的场景。
陈维广:做到这些,不仅任务完成率要接近 100%,边际成本也要可控,ROI(投入产出比)如果不合理,客户会觉得不如用人来完成任务。
晚点:什么时候具身智能机器人会到这个状态?
朱天宇:快的话,2025 年内。
晚点:最先落地的可能是什么形态的机器人?人形、类人形还是其他?
朱天宇:(形态)其实不重要,关键还是看,智能机器人到底有什么能力,能完成什么任务。
项目估值遵循 “幂律分布”,在 AI 里抓 “塔尖投资”
晚点:蓝驰 2008 年成立,在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的 “捕鲸时代” 里,错过了一批千亿、百亿美元明星公司,如阿里、京东、字节、拼多多、快手、小红书,至今却依然活跃在牌桌,管理规模从几千万美元扩张到现在的 200 亿人民币,这是怎么做到的?
陈维广:最终一个基金的生命力是要兑现到 DPI 上,也就是给 LP 的实际回报。我们也在持续迭代认知。早年没投进这些项目,有资源限制,也有认知局限。当时支票小,投的是更早期的项目,错过了部分估值迅速拉高的公司。
晚点:你们早年投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的经验和教训,对今天投 AI 的影响是什么?
朱天宇:意识到 “贵” 并非坏事。2015 年之前,我们更多是投首轮、投早期,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项目,我们除了蚂蚁,应该都见过,但不少项目的估值已超出我们的出手区间了。但后来我们意识到:即便头部项目估值高,但它的市场地位、团队势能和竞争优势会持续增强,反而更值得加注。
晚点:其实你们后来连投理想 5 轮,就是从投早到持续加注头部项目的变化?
朱天宇:对,理想很吸引我们,不是因为它是新能源车公司,而是它从一开始就强调数据闭环、自动驾驶,以及李想本人对组织能力的重视。他经常主动聊组织建设,有很强的战略思维。我们最大的加注是在美团入局前,风险最高,但我们看到了理想团队的执行力和快速迭代能力。
2020 年底我们做过一次系统复盘,截至当时,整个中国市场长出了 6 家千亿美金公司、30 家百亿美金公司、150 至 200 家十亿美金公司,呈现出典型的 1:5:25 的幂律分布。这让我们更笃定 “塔尖策略”。但当我们准备按这个逻辑加大投入时,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。直到 2022 年底 AI 崛起,才让 “押头部、投最前沿” 的策略真正可以实践。
晚点:现在你们在 AI 和机器人领域出手更激进,比如它石的天使轮就融了 1.2 亿美元,估值也很高。你们现在怎么定义 “贵”?
朱天宇:我们看的是整体策略,而非单个价格点。关键是这个方向是不是我们坚定看好的、这个团队是不是能真正交付东西。一个简单的常识是:便宜但不能落地的项目等于亏钱,贵但能做出结果的项目,更有投资价值。
晚点:AI 和具身领域,是否已经出现了字节、拼多多这类会被没投到的机构都视为大遗憾的项目?
朱天宇:Agent 方向,可能会跑出这样的公司。这波 AI 跟上一轮移动互联网有本质不同。上一轮的核心是 “连接” 带来的规模效应和平台垄断;而这一轮的核心在于 “生产力” 跃升。Agent 代表智能真正介入生产的能力,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重构产业链和价值链,潜力不止千亿美金。
陈维广:很难一开始就看清楚赢家是谁。1995 到 2005 年,我在硅谷待了 10 年,当时大家看好雅虎,没料到后面还会出现 Google;我们投的 PayPal 上市后,市场也觉得电子支付差不多了,后来又出了 Stripe。AI 现在还在早期阶段,是基础模型胜出、还是应用驱动、还是模型 + 应用并行,还未有定论。
晚点:在整个 AI 领域,你们看到的相对确定的趋势是什么?
朱天宇:大模型的 coding 能力正迅速增强,这可能引发一场 “暴乱式” 变革。因为当 Agent 有强大的编程能力,它就能重构各种系统,像野火过境,为下一轮应用爆发奠定基础。
“我们不是兔子,是慢慢迭代、但不断向前的乌龟”
晚点:1999 年前后,你在硅谷完整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高峰和破灭,这和现在的 AI 热潮哪里相似,哪里不同?
陈维广:其实 1999 年的互联网热潮,并不是硬核技术驱动,更多是建站。那会儿互联网技术已发展了相当一段时间了。而这之后,从 1999 年的硅谷,到移动互联网,再到新能源汽车、智驾,再到 AI,变化速度越来越快,压缩了技术研发到产品化的周期。所以 AI 的节奏,很难完全参考当年的互联网。
晚点:它比较像科技史上的什么阶段?
朱天宇:我觉得比较像上世纪 70 年代,大型机到个人电脑的转变,只不过那是十几年的演进,现在大模型的变革可能被压缩到短短几年内。
陈维广:我当年在 IBM 负责 PC 产品,刚好经历过那一段。搞大型主机的人普遍不看好 PC,觉得只是玩具,IBM 也没把 PC 当主业。那时银行的终端都很 “傻”,改功能要等几个月让 IBM 工程师来改,IT 部门权力极大。后来乔布斯、苹果推动了 PC 普及,5 到 8 年间突然拐点出现,谁没跟上节奏,谁就被淘汰。IBM 后来能活下来,是因为及时转向 IT 咨询,不再死守硬件。
这和今天看具身智能的视角很像:不少人会觉得 “太早期”、“不可能”,但一旦变化启动,再跟就来不及了。
晚点:你后来在 2008 年成立蓝驰中国,这是你第一次长时间来中国,为什么当时想要来中国做风险投资?
陈维广:对,我是新加坡人,刚来中国时,普通话比现在还差。我在国内(指中国)一个人都不认识。但当时在硅谷,已有不少华人工程师和科学家陆续回来,每个月都有欢送会,而且回来的人的质量越来越高,VC 要跟着人才走;第二,坦白说,蓝驰当时在美国不是一线 VC,所以我想来中国寻找机会。
晚点:那时候一批美元 VC 在中国建立的分支,如红杉、GGV,近年都面临变得更独立和本土化的议题。蓝驰是怎么经历这个转变的?
陈维广:蓝驰和其他机构不大一样。早在 2012 年,我们中美两边的募资、管理和投资就完全分开了。之所以还沿用 BlueRun 品牌,是因为我在硅谷做了 10 年投资,跟美国合伙人关系好。
后来 2023 年,我们把品牌英文名从 BlueRun 改为 Lanchi,更多是出于运营考量,我们实际投资是分开的,但不少数据库和媒体会把中美两个蓝驰的项目混为一谈。我们的独立是更早、也更内生的过程。
晚点:20 年过去,和蓝驰同一批来中国的一些机构早不再活跃,也有一批和您同辈的投资人近年陆续退休,为什么你还在一线?
陈维广:我觉得做 VC 不只是追求回报,更要有使命感,你得真心喜欢这件事。这个行业挑战大、风险高,像你提到的机器人现在也没那么 “性感”,但我们还是愿意投,是因为相信一些团队和方向。
我每天还在见项目,尤其这代 AI 创业者,很多是 1998、1999 年出生的年轻人,跟他们交流,我觉得自己也能不断更新。能持续在一线,是因为我享受这个过程。
如果把 VC 比作赛跑,我们不是兔子,是乌龟,慢慢迭代、不断往前爬,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
晚点:如果兔子不睡觉怎么办?
陈维广:不一定是兔子要睡觉。其实这条路不好走,可能兔子觉得其他的路是捷径。但乌龟对它的道路非常笃信,一步一步坚持到那里。就像你也知道,2017、2018 年之后,确实很多人对科技发展产生了一些担忧
晚点:别人担心时,你为什么还有信心?
陈维广: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华侨,在新加坡长大,美国待过,看到过华人在全球的奋斗。我很认可中华文化,我觉得华人的韧性和创新性都非常强,我对中国做硬科技始终看好。
晚点:在 AI 浪潮里,你想让蓝驰发展成什么样的机构?
陈维广:这次 AI 变革堪比工业革命,它能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。我们的目标是找到那些 “六边形战士” 的创业者——既有全球视野,又能深度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,带来实质性的产业提升。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成长,这本身就是一种满足,也一定能带来好回报。
晚点:你不追求通过 AI 机会让蓝驰变成最一线的 VC 吗?
陈维广:我们更在意的是长期的认知积累和组织成长。这 20 年,我们一直在慢慢变强,对我来说,这是最大的成就感。
晚点:你有给自己设置过退休时间吗?
陈维广:没有。我常跟同事开玩笑,如果有人爬山能比我快,也许那就是我该退
文章来自于“晚点LatePost”,作者“程曼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