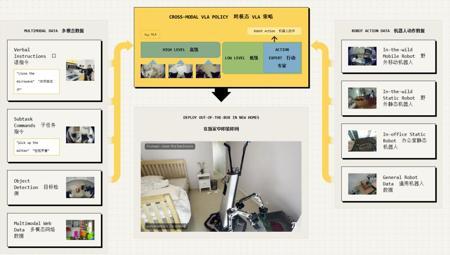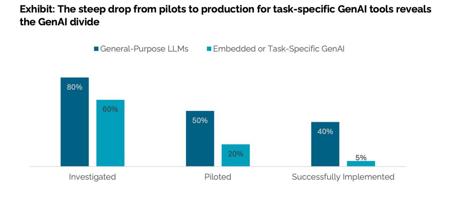英国《卫报》专栏作家玛丽娜·海德(Martin Naumann)撰文指出,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·奥特曼(Sam Altman)虽然在以惊人的速度重塑AI格局,却深陷版权盗用、政治投机与伦理泥潭等指责。
OpenAI的Sora 2文生视频模型技术惊艳,却暴露了AI对创意产业的掠夺本质。海德犀利剖析:OpenAI的“后版权”(Post-rights)逻辑正威胁全球文化。如果它代表未来,我们是否已无力回天?
以下为文章全文:
请认真的看看山姆·奥特曼。
打开谷歌图片,你会看到这位OpenAI首席执行官的无数照片。他带着一种介于天才与冷漠之间的笑容,看似谦逊,却透出一丝令人不安的傲慢。他眼睛里的神态,像极了那位谎称女友失踪、实则把人藏在自家地下室,却还对着镜头装出无辜样、恳求她“快回家吧”的男友。
我这样写,实则是讽刺OpenAI那套名义上保护创作者、实则无效的“选择退出”机制。
我曾就此事尝试联系奥特曼本人,但他一直没回我消息,所以我推断,他对我这样形容根本没意见。说到底,他正一点点显露出那种熟悉的气质:赤裸裸的自负,几乎不再费心去掩饰。
过去两周,奥特曼发布了AI文生视频模型Sora 2。与10个月前的第一代Sora相比,Sora 2的升级效果堪称惊艳。该模型一经发布,就立即引发了大量关于其训练数据版权侵权的争议。
OpenAI还同英伟达、AMD等公司宣布了一系列循环交易,使其总交易额在今年的AI热潮中突破1万亿美元。但这种资本狂热也可能孕育泡沫,一旦破裂,其冲击或将超出AI产业本身。
我对Sora的“创作者”绝没有冒犯之意。我经常逛艺术画廊,常会意识到墙上的作品要是我直接偷走,或者再添上些滑稽的涂鸦或其他恶搞内容,反而会“好看” 得多。要是他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,当初就不会公开展出作品。
而科技巨头们本就缺乏文化生活,自然无法理解:有些创造性价值,是你绝不希望被机器人为了逐利而亵渎的。你要是看过奥特曼常推荐的书单就知道,那些书其实就是二流机场书店里“商业哲学”区随处可见的货色。
到了本周,他则一心想让大家知道,Sora 2非常酷、也非常有趣。奥特曼甚至还在社交媒体X上发了条帖子:“看着满屏都是自己的梗图,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奇怪。” 这么看来,一切似乎都好得很!
不过我想,如果你是世界上最有权势、身价数百亿美元的人,你的处境肯定比现在好得多。你根本不必担心,会像我这样,因为系统错误或限制不清,在复杂的虚拟环境中遭受恶意侵害。
我曾看到有人说,OpenAI的座右铭应该是“先斩后奏,好过事前请示”,但这美化得荒谬。
OpenAI真正奉行的逻辑是:“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你只能接受。”
回顾一下今年年初的事:当时有迹象显示DeepSeek,可能是基于OpenAI的技术成果训练而成。OpenAI曾煞有介事地发表声明:“我们已注意到DeepSeek可能不当提取我方模型的迹象,目前正展开审查;一旦掌握更多信息,我们将及时分享。”
该声明还强调:“我们正采取积极、先发制人的反制措施,以保护我方核心技术。” 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,放眼全球,似乎唯一有能力打击AI盗窃行为的实体,竟然只有OpenAI自己。这话听着实在荒唐。
本周,好莱坞人才经纪公司总算让奥特曼暂时退让了一步。
他说的话含糊不清,只提会试着给那些他公开称为“版权所有人”(Rightsholder)的群体,一些“新的参与途径”。
“版权所有人”顾名思义,就是那些真正拥有创作权的人。可奥特曼搞的是“后版权时代”的一套。OpenAI对知识产权的漠视,正在引发更深层的担忧:当一个企业可以无视创作者的权益,它是否也会无视用户乃至公众的权利?
OpenAI真正想要的,是所有大型平台最终都想要的:成为互联网的核心。它正在将自己定位为互联网的新默认主页,就像当年的Facebook一样。
在这种情况下,Facebook曾引发的那些危机,比如虚假的“有爱心”成长故事、隐私泄露的恐怖秀,以及对儿童的伤害问题还会远吗?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个生命周期。但我们可能要再经历一次。或者,更准确地说,鉴于OpenAI的空前发展速度,我们又要再次经历一次。最开始,我们总夸某位神秘的科技从业者,说他是个杰出又特别的“好人”。结果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:他根本不是表面那样,他的技术也比预想中危险得多。
可我们还没做好监管,现在已经成了这技术的受害者。这一切更像是一部我们早已看过的科技惊悚片,只是这次,剧情由AI亲手导演。故事的剧情套路都差不多。既然AI模型都能自我学习,人类又为何总是拒绝吸取教训?
本文来自“腾讯科技”,作者:无忌,36氪经授权发布。